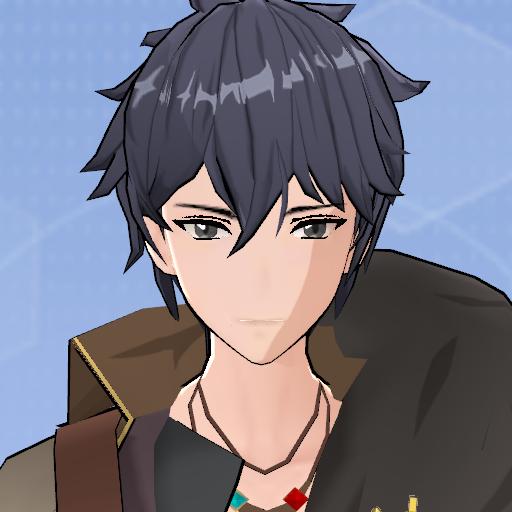5岁那年,在一场意外中,钰坤的右手断了4根筋。因此,本该在幼儿园学习拼写的他只好在家养伤。期间,钰坤接触到计算机游戏,通过《极品飞车》和《生化危机》,他完成手指的术后复健,也就此迷上光怪的游戏世界。
2008年,钰坤13岁,读初中。出身书香世家的父母对钰坤抱怀期望,不知他心思早已飞出校园。开过几次家长会,钰坤的父母终于发现,虽然儿子每天按时背着书包离家,早出晚归,但大部分时间他都泡在网吧里自学编程。

▲14岁辍学做游戏赚到第一桶金,钰坤总是归因于运气
少年钰坤算过一笔时间帐。假设老老实实在学校读书,大学考计算机专业,毕业后进入社会时自己二十多岁,简直晚得浪费时间。当时他痴迷学习编程等计算机技术,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,醒来浑身充满了劲,感觉未来光明可期。
但钰坤的父母可不这么想。大好青春不读书,就想去做社会青年?父母决定经济制裁他。
那时候,钰坤与论坛上结识的游戏爱好者结为同伴,借助一款JAVA模拟器,他们写了多款游戏脚本,很受欢迎,用户自发付费,平摊下来,每人每月都能收入几万块。失去家里的经济支持,钰坤非但没有受困,还给父亲买了一部智能手机。
父亲问钰坤,究竟读不读书了?他当机立断:“不读了。”
因为辍学专心做游戏的决定,钰坤成为同龄人里的异类,但在游戏行业,他一度是最年轻的前锋。17岁,曾经的同学正焦灼地备战高考,而他已经烧光了创业赚得的第一桶金。
如今,钰坤选择进入MetaApp公司担任研发工程师。这是一个面向全年龄段的UGC互动内容创作和体验平台。在这里,像钰坤一样在少时入迷,将游戏视作毕生理想事业的同事占据多数,每个曾经的游戏少年,都希望能在这场人生事业里建造自己的巴别塔。
光齐,24岁,是MetaApp编辑器的产品经理。和钰坤一样,还在读小学时,光齐靠纸笔游戏就赚得了第一笔收益。
毕业后他花了很大力气才让父母同意他留在北京打拼
光齐的父母、外公都是老师,和游戏天生是劲敌。为了能顺畅地玩游戏,光齐得保证自己的学习成绩考得上重点高中,同时跟家里的老师长辈们谈判,“我在学习如何使用一些插件的时候会去找全英文资料,靠机翻和联想,掌握了大量不可能在课本里学到的单词和语法。”
光齐最喜欢的游戏是《我的世界》。第一次进入服务器的时候,他感觉,突然这个世界就打开了。“它带领我去往一个和现实世界不一样的地方,从现实的孤独,走进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。”光齐的家乡是江西吉安的一个小县城,接触游戏前,他在学习之外的唯一消遣是逛公园,“ 在那个小镇逛来逛去就只有那一个公园。”光齐觉得,游戏像水一样,滋润了他原本荒漠化的生活。
高二,光齐随县城的游学团去过北京。那一次,在长城上,售价40多块钱的“天价”矿泉水让光齐“很长见识”。“一瓶水,在我们小县城就一块钱,到北京的餐馆里变四五块,到长城上就能卖到40多块钱。”光齐由此思考,人的价值会因为用途和位置而改变。
高考填报志愿时,光齐特意填了北京的学校,可惜最终没能考上心仪的计算机专业,而是学了地质专业。
父母希望光齐毕业后考公或者考编,但光齐自认社恐,老师、警察、医生这种大家公认的好职业,每天要跟各种各样的人高频次接触,对他来说非常困难。而游戏是能给他充电的港湾。大学期间,他和朋友共同制作了一个游戏服务器,可观的收入和常驻玩家的支持给予了他信心。
游戏的内核不是孤独,不是逃避现实,而是一种交流,光齐也这么觉得。他说,虚拟世界里的光真正照进了他的现实。
2021年12月,光齐加入MetaApp成为虚拟社区的产品经理,在面试过程中,他和三位面试官聊得前所未有的开心。好像见到了游戏世界里才会遇到的同伴,大家都有共同的理想,共同的愿景。HR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入职,他说:“明天就能来。”
起初,光齐想成为一名游戏策划,他认为,这个世界上不缺程序员,但缺有想法的人。加入公司后他发现,自己太幼稚了。这个世界上有想法的人特别多,而且想法各有各的好。
猫叔28岁,做游戏策划,他最初的目标是名留青史,但入行头两年,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对着Excel填数,写公式,看数值体验有没有达到设计目的。很长一段时间,他认为自己的工作几乎跟打字员、外卖员、司机没什么区别。
▲猫叔是一名资深的游戏策划,他认为做出一款成功的游戏,比中彩票还难
游戏带给玩家的快感是多维的,但游戏系统背后,各个工作岗位单一且垂直,游戏做得越复杂,背后的工作可能就越庞杂枯燥。光是“游戏策划”这个岗位,就可以细分成主策划、系统策划、数值策划、文案策划和关卡策划等。
▲猫叔突然灵感爆发,兴奋地拉着同事开会分享想法
跟光齐想象的不同,无论哪一类细分的策划岗位,都非常考验沟通能力。猫叔经常跟刚入行的新人解释,游戏策划相当于一个大脑,需要把命令精准地传达给下游同事,可能是游戏美术,或工程师。而沟通只是基本功,要成为一名称职的游戏策划,你还要有严密的逻辑性。
像贪吃蛇那样看起来很简单的游戏,设计起来也不简单,“蛇吃到尾巴会死,碰到外框会死,基于这个规则,需要在逻辑上规避一些bug,比如不能让吃食物这个事情频繁的出现死局,还要控制蛇的爬行速度让玩家玩起来既不觉得太快,又觉得难度有增加,还得保证乐趣。”
光齐在做的工作就像是做侦探,“哪个数字波动了一下,我就要去找波动的时间线上发生了什么,一点点查,排除干扰项,最后把原因归到某一个指标。”
这是光齐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职业选择,他认为,在这个位置,可以辅助同事提升玩家的游戏体验。每天上班,他需要盯着电脑上的相关量表和线图找异常,将问题反馈给工程师同事去做修复,让异常慢慢回归正常水平。
做游戏跟玩游戏完全是两码事。备受捶打,几乎是每一位游戏人在入行之初都会有的体验。2021年5月,25岁的段仲成为一名新人策划。第一次写策划案,段仲像写小作文一样,堆叠各种修饰词汇。第二天,前辈拿到她的策划案,一直在笑。
段仲这才知道,在游戏策划里,文学性修饰是最不重要且不需要的。等到跟开发部同事对接的时候,她头更大了,同事说她的策划案“很烂”,而她连对方说出的专业词汇都没听懂。
▲因为游戏玩得不错得到了同伴的认同,游戏成了段仲的现实生活的避难所
段仲觉得自己特别丢人,只好私下用功,学习写代码,用工程师能够理解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。再去跟研发同事对接的时候,他们角色互换了。“我说要做一个需求,他们跟我说太难了,做不了。我说这个真的难吗?真的不能做吗?”
遇到难以妥协的情况,段仲会做大量的调研寻找数据支撑,来判断自己的想法是否成立,她也不希望自己脑子一热提出个伪需求。而一旦经验证得出她的想法是对的,遇到任何阻力,她都会不遗余力地往前推进。
▲段仲的同学很羡慕她有一份独特的工作体验,
因为学的师范日语,大多数人会选择留在老家当老师
入职前,段仲给自己写过职业规划:入行一年成为中级策划,两年成高级,三年变主策。现在想起,她只觉得搞笑,“像小孩子在说大话。”当时她以为事业进步就是职位往上爬,直到见到那些目标中的“高级策划”,她才发现,他们只是背负着更大的责任,要做的事情更难。
先前,段仲在北京上班,房子租在望京的老旧小区,一个月3000块,卧室里只能放下一张桌子一张床,连多一台主机和显示屏的空间都没有,而这样的价格在她的老家能租一栋大三居。晚上下班回家,她还常能在单元门口碰到喝醉的大叔,手里捏着钥匙说,“妹妹帮我开下门”,很恐怖。有大半个月,她焦虑得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。
▲下午六点的望京地铁站
在北京生活,对段仲来说,有点像赌博,她没有底气,也没有底牌,除了把青春的时间耗在这里。“像要在游戏里打一个很难的副本,你在里面会觉得很紧张很局促,很不安。而你都不确定它里面有什么奖励,干嘛呢?”
▲段仲喜欢在街头寻找制作游戏的灵感
还好,公司在成都和北京都有办公室,段仲毫不犹豫地选择转去成都。即使工作中的摩擦还是难以回避,但来到成都后,段仲明显感觉,自己的情绪比过去稳定多了,学会去理解各种各样的观点,也不再陷入精神内耗了。
即使没有北漂、还车贷房贷等现实压力,进入游戏行业,仍是一个具有“赌”性的选择。岁寒和段仲差不多同一时期进入的公司,她在北京出生长大,吃住都在家里,几乎没有经济上的压力。作为一名中传科班出身的游戏策划,还没毕业时她给自己定的薪酬目标低到别人听了都不忍心的地步,“我想我每个月能赚5000块钱,就非常开心了。”
▲毕业前岁寒对薪酬要求很低:“每个月能赚5000块钱,就非常开心了。”
入职后,岁寒的实际收入远高出自己的预期,但压力也紧接着跟上来了。虽然公司里年轻的策划不少都是女性,但往上看会发现,高层里很难见到女性的身影。少了未来的参照,她心里没底,想象不出如果一直做游戏策划,几年之后自己是什么样子的。
▲工作中的岁寒。科班出身的她,做游戏策划成了顺理成章的职业
单论工作本身,岁寒并不觉得男性比女性有更多优势。岁寒正在做的项目中,程序组长也是女生,从业多年,代码技术非常优秀。
不久前,刚上线的项目查出60多个bug,连续数日,岁寒忙着逐一排查问题,这种紧迫感让她回到家倒在床上就能睡着。外地人觉得在北京待着压力太大,还能回到自己老家,可岁寒只能撑住,继续打拼,因为北京就是她的家。
岁寒认为,做游戏的使命,是让玩家在游戏里感受到快乐和丰富人生体验。这不一定非要依靠需要巨量运算的大场面。岁寒期望可以善用自己细腻的特质,做出细节更到位,更顺滑舒适的游戏设计。
▲面对高昂的生活成本,段仲决定离开北京去成都
事实上,段仲和岁寒不是少见的女性游戏策划,越来越多女性从业者进入游戏行业,性别偏见正在逐渐被打破。曾有一位前辈,对段仲的评价是“出类拔萃”“以后招人就要按她这个标准去招”。
段仲感觉,那是近几年,自己最高光的时刻。
在猫叔看来,游戏策划是一个“很局限”的工种,25到35岁之间是黄金年龄,随后会进入创意的衰竭期。今年猫叔28岁,事业发展很快,但在北京他很难有安身的感觉。
租着房子,拿着一份相对同龄人还可以的工资,有时忍不住搜一下房价,10万一平米。猫叔说,不可能有人不挣扎,甚至,很多漂泊的人从踏入北京第一脚就已经在思考,未来从北京离开的时候要怎么办了。
▲早上9点的望京
当猫叔逛街探店寻找美食的时候,会下意识地审视店家的装修,还会考虑菜单定制的逻辑,定价是否让人产生购买欲,介绍菜品的顺序好像不是特别舒服,摆件如果那样摆就更好了......他想,如果有一天自己离开北京,离开游戏行业,可能会选择开一家别致的小店。
比如开一家酒吧。猫叔觉得,酒和游戏一样,都是能让人释放情绪的东西,调酒和游戏策划有相似之处,也是情感表达。“......这杯酒偏甜,但是回口苦,或者这杯酒特别烈,名字叫绿帽子。”
像对待一个爱不释手,又恐怕会失去的礼物,很长一段时间,猫叔职业焦虑严重。而能够帮助游戏人缓解压力的,依然只有游戏。
一个晚上,猫叔玩了两个小时的《风之旅人》。这款游戏中,玩家扮演一名旅者,穿越沙漠,翻越高山,走过无数桥梁桥梁,不断寻找、唤醒旅途中遇到的碑文,以加强自己的飞行能力,抵达旅途的终点。
▲望京附近立交桥的最后一班地铁
游戏结束,猫叔获得了一种震撼的平静。“我能感受到Ta在做游戏时有过的痛苦跟挣扎,能感受到Ta生活中有过的成长跟兴奋,我真的能在这个游戏里面获得共鸣,像读一本书。”
小时候,光齐家境普通,没有钱买玩具,他于是自己折纸、做木工,制造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东西。因为物质的匮乏,他没信心和班里的同学建立交流,自我封闭的青春期,他在虚拟世界里进行精神探索,认识了很多好朋友。
和女友刚在一起的时候,光齐常常送给女友手工做的礼物,不贵重,做起来却很费时间和心思。女友特别开心,后来也偷偷给他手工做了个温馨的小家,里面放了两只小兔子,跟光齐说:“一个是你,一个是我,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小家了。”
光齐明白,这是感情的托付。
去年9月,女友出国读研,两个人开始异国恋。每天晚上,结束和女友视频通话后,光齐就打开编辑器,按当初女友送自己的手工小家为原型,在虚拟世界搭建了一个复刻版的家。
女友生日当天,光齐一步步引导女友登陆,进入他为她搭建的家。网线两端,相距8000多公里的两人得以相聚。女友坐在沙发前,闭上眼睛,光齐端出了生日蛋糕。
在虚拟的家中,光齐为女友办了一场生日派对,“虽然Party只有我们两个人,但两个人,就有一个世界了。”而他相信,未来,他还能在这个虚拟世界里继续探索更大更远的边界。